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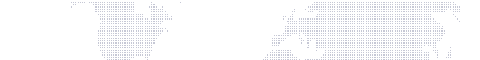
| | 网站首页 | 文章中心 | 学术动态 | 资料下载 | 建议留言 | 文化论坛 | | |
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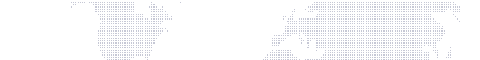 |
| 您现在的位置: 文化中国 >> 文章中心 >> 文学研究 >> 文学理论 >> 文章正文 |
|
|||||
| 劉勰與易經再論 | |||||
| 作者:游志诚 文章来源:本站原创 点击数: 更新时间:2004-5-21 | |||||
|
【提 要】 劉勰字彥和,一生之思想來自易學,學術論述亦本乎易理。學說之基本架構皆不出易學。劉勰一生思想之綜合,可歸之「子論」之學。劉勰寫作《文心》、《劉子》走的是「子論」系統,非自限於集部之學。《文心》、《劉子》兩書之篇數,一用大衍之數五十;一用天地之數五十五,兩書之中心思想,一舉〈原道〉,謂自然之易道;一立〈神清〉,用易道之「神」義。兩書明顯用易學思想,可證劉勰之子論,溯源自易經,思想本源出自易學,兼包儒道。 【關鍵詞】子論 性情 原道 易經的心學 文心 易經之學是劉勰文藝思想本源。易貫儒道二家,凡屬於「九流」之學者,其性質皆近乎「道」,而此道即易之道。凡由易之道繁衍而成之學,皆是「子論」之學。劉勰一生思想之綜合即歸之「子論」之學。而非宗教之學。 子論非等於宗教。子論關注心神,宗教則關注形神。子論涉體性,宗教志在鬼神。子論兼攝九流,宗教則排彼破彼。此在六朝學術文風乃習見之現象。今試括舉數端以證劉勰以易為宗之文藝思想。 一、自向歆父子「七略」之分,學術分科概念,孳乳而下,又有荀勗四部分類,經史子集之別益明。至葛洪《抱朴子》外篇首揭「子論」之名,使與「詩論」判分。「子論」之學既立,實包括「言辭」、「文苑」,即今之文學。蓋六朝以前,文集專論,或曰詩論,詩品,文章流別云云。集部之學勒成專論尚未成氣候。雖有《文心雕龍》之作,但經史子兼說之,劉勰寫作《文心》走的其實是「子論」系統,非自限於集部之學。文心如此,《劉子》當然也屬「子論」之作。兩書相較,思想本源皆出自易學,兼包儒道。思想系統相同,故而兩書之作者實同一人。 二、子論與宗教可以並行,但宗教與宗教之間必互相排擠而不見容,此實為六朝學術風氣之一般現象。故而劉勰雖作《文心》與《劉子》,不害其又有〈辨惑論〉之構。前者劉勰乃子論家之學,後者劉勰個人一生信仰之「終極關懷」問題。 三、《文心》、《劉子》二書之篇數,一用大衍之數五十,一用天地之數五十五。兩書中心思想,一舉〈原道〉謂自然之易道,一立〈神清〉,用易道之「神」義。兩書明顯用易學思想。可證劉勰之子論,溯源自易經。劉勰雖參與校訂佛典,入僧佑門下,廁身定林寺,並有〈滅惑論〉之作。此劉勰個人之宗教信仰必然之行為。但劉勰終究是子論家,且不因此而妨礙其宗教信仰。子論與宗教在劉勰而言,實乃一人之二事。 以上三端所示,說明劉勰一生之思想來自易學,學術論述亦本乎易理。基本架構皆不出易學。引而伸之,《文心雕龍》全書重要術語概念,亦大抵源自易經,發揮旁通,博參引證,以建立文心之文論。 例如《文心雕龍》一書屢言性情。性情一詞之概念,與陰陽五行之說有涉,當然也是易學的課題。然而,龍學家對此多未深究,以致各家錯解異解之言,隨處可見。 〈情采〉篇謂形文聲文情文,各出自於五音五色五性之說,其中究竟作「五性」或「五情」?又何為五性五情?說者最見分歧,皆因不能據易學以判讀之故。此即龍學與易學宜相並參之又一例。 〈情采〉云:「三曰情文,五性是也。」又云:「五情發而為辭章。」,此二句之性情每見注家混解之。首先,後一句「五情發」,元至正刊本作「五性發」,今經楊明照據前人本(如王惟儉)校改五情,從者甚多,大抵定論無疑。問題在,何謂五情?蓋易學所知者,僅言「五性六情」,並無「五情」之說[1]。對此,且觀龍學界諸解二、三家如下: 詹金英 《文心雕龍義證》引《文選》曹植〈上責躬應詔詩〉劉良注云五性:喜、怒、哀、樂、怨。(頁1152。)此注之五性實即五情。祖保泉《文心雕龍解說》引《大戴禮·文王官人》謂喜、怒、欲、懼、憂為五性。(頁610。)此與前注類是。王更生《文心雕龍讀本》注云五性是指仁、禮、信、義、智。(頁80。)此當是五禮或五倫。李曰剛《文心雕龍斠詮》始備引《漢書·翼奉傳》之「五性六情」語,晉灼注云: 翼氏五性,肝性靜,靜行仁,甲己主之,心性躁,躁行禮,丙辛主之。脾主力,力行信,戊癸主之。肺性堅,堅行義,乙庚主之。腎性智,智行敬,丁壬主之。[2] 此解最是,不但注明五性與五行之相配,且兼明五性與天干之運行。尤有甚者,天干化合之說亦在其中。諸如甲己合土,乙庚合金,丁壬合木,丙辛合水,戊癸合火。天干五行相配,更兼及五行相生相剋之理。如甲木主肝,行仁。甲己合土,乃春木宜生於土,故曰甲己合土。丙火主心,行禮。丙辛化水,乃心火欲其靜不宜躁,故以水剋之。戊土主脾,行信。戊癸合火,蓋脾胃忌寒喜溫,故引火暖之。庚金主肺,行義。乙庚合金,乃因金氣宜洩不宜扶,故配乙木受剋而洩其力。至於壬水主腎,行智,丁壬合木,蓋欲水木相生,以增春意。以上天干化合,五性五行配合,環環相生相剋,以達生生不息之理,當即易學之發揮。而為《文心雕龍》之所本,以闡述文章情采來自作家情性,因性因情,文采不同,而莫不互為相生,以形成煥煥然眾家各具面貌之態。《文心》據易理以述明文理之證,有如是者。 故而〈情采〉篇此處所云五性,當指五行之性。即木火土金水五行之人。由之相配之五志(五情)即:怒、喜、憂、悲、恐。亦即:靜、躁、力、堅、敬五類性格之別。由此五行五性衍生之五倫五品,始可言曰仁、禮、信、義、智。五性即五行之性,龍學諸家注何以未得盡解?乃緣乎易學易理實為《文心》一書之大本而不知,或雖知而不信。[3] 《文心雕龍》一書首立文之綱領,曰〈原道〉。此道為何道?歷來說者不一,己見多篇論文,茲不贅述。今所辨者,引《周易》之道,援《周易》之理,以進一解,幸有助乎龍學「綜合研究」之一途。 今案〈原道〉篇所言之道,關鍵句在「心生而言立,言立而成文,自然之道也。」一段。此一段有「心」字、「言」字、「文」字等,皆古代思想史重要概念,訓解失偏,不辨來源,即易混解或錯解。在台灣的龍學研究史上,對此一段文心原典的理解,所引發之文心全書理論爭辯,最具體之例,即王夢鷗與徐復觀二家之疏解。[4] 王夢鷗據此段認為彥和的文學定義是「語言」,並且,人因為要抒發「語言」,而產生「文學」,這一過程是自自然然不過的事。故而文心之〈原道〉,乃是語言自然之道。 徐復觀不同意此解,認為此段話是就上文總括天地皆有「文」,人為五行之秀,秉天地之心,當然也有「文」。但此一境界之「文」,僅僅只與「天文」、「地文」同層次,故而只備「原始人」、「初生人」之文,並沒有藝術性。《文心》〈原道〉只是先闡明人之有「文」的來源,接下去全書之安排架構,即在討論文的「藝術性」,所以彥和作《文心》,便是要研究這個文的藝術性問題。徐復觀總結《文心》的的文學定義重心是在「文體」而非語言。 以上二家之歧見,看似南轅北轍,其實無不各自成說,且如明月溝渠,各照隅隙。而問題就出在未把此段關鍵文句連繫到《周易》去理解,未從易理的源流發展去疏釋關鍵概念,因而導致之誤判,或者不足。試想此段文心原典,若將「自然之道也」一句改為「(文)道之自然也」,文義朗然,即不致引生異說矣! 何則?〈原道〉全篇言文之道而已。此道非關儒、釋、老莊之道。實則只有一個「易之道」。但因彥和生當魏晉玄學熾盛學風之際,談文論藝,搦筆言文,為著「駢文文體」修辭之便利,不自覺雜揉玄學語彙,積染成習,蓋乃不得不然之勢。致易理原義不明,令讀者引生歧解,此即問題所在。 其實,《文心》的道只是文道。然則文道如何來?〈原道〉篇之立論悉本之《周易》架構。《周易》首揭天文、地文、人文,謂之三才。文之外,又立天心、地心。此即〈復〉卦所言「復其見天地之心哉」之心。既然天地有心,人亦當有心。故而人心與天心地心相仿,並而為三心。又因天有文,地亦有文。天地之文假想出自人心。此即「心生而言立,言立而成文」之發展過程。簡言之,〈原道〉首揭文之道來自人心,人心來自道,道即易道。人文天文地文皆出自易道,或即《周易》所示之道。此道,自然而存乎天地人三才之當然必然而有者。故曰「自然之道」。彥和以為文學之初始本源來自人有「心」,人之此心順隨天心地心而併立。既然天地有自然之文,如「雲霞雕色,草木賁華」一般自然,無待人工琢磨。那麼,人心必能產生「文」,所謂「形立則章成,聲發則文生」之原始人文,乃是順理成章之事。彥和講「自然之道」即指這一層含意。非關什麼儒道、釋道、老莊玄道。[5] 道既是來自易經,天文地文人文都是「〈易〉道」之自然。然則從文到「心」之過程又是如何呢? 彥和取「文心」為書名,雖含有「言為文之用心也」之義。但這個「心」,是指的「天地之心哉」。也即是說文心與天地心是相同的。天地心的始發首倡者,在《周易》,當然,依此類推,文心也來自《易經》。這一見解,對照曹丕的「文以氣為主」,范曄的「文以意為先」之魏晉文論,絕然是文論進展上的一大創解。可以說,彥和的「文心」論,在古代文論史上居於關鍵樞紐位置。無怪乎紀昀對此有評云:「自漢以來,論文者罕能及此。」就此一論點而言,彥和不但點出文學來自易道,反之,彥和也間接論證《周易》一書的文學成份文學價值,易經是文學,不只是講哲理的易學而已,這在易學研究史上也是最早提出者。紀昀有評云:「解易者未發此義。」甚是。簡言之,彥和在〈原道〉篇率先提出文學來自易經,易經也具備文學性質的雙重創解。 然而從「文」到「心」之過程,又是一大轉折。文來自《易經》,心也是《周易》首言之。《周易》談「心」的幾卦,結合其它古代文獻並參,如《管子》、《左傳》、《荀子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大學》等。即可看出,先秦有一門「心學」之脈絡,隱隱然匯為暗流,下貫到後世之義理學。中間轉化到文學一路的論述。可以說,《文心雕龍》一書,援「文心」之道以立論,即最具代表性者。 今請述易經心學與先秦心學文獻之要義如下: 易經心學,主要見於〈坎〉、〈離〉、〈益〉、〈復〉四卦,其中又以〈坎〉、〈益〉二卦言心最有深義。此二卦講心的功夫,如何損益?如何充實?〈益·九五〉云:「有孚惠心,勿問。元吉。有孚惠我德。」此處之孚即信誠意。劉沅謂即:「有至誠之惠心。」姚鼐亦云:「中心至誠,以順民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,不必盡人問之也。」[6]姚、劉二家說,皆扣緊心與誠之關係。做為天地人共通之「心」,如何發揮心之作用,在人而言,即是「誠」字之功夫。心學以「誠」做功夫方法,到了《中庸》終於定下來。所以說,《中庸》的誠,是孔門心法。然則〈益〉卦中的「心」,只要存乎天地之心即可,太過則損,不足則益。始終要保持「不盈」的狀態。可見〈益〉卦的心,講究「虛心而受」的不盈功夫。 彥和繼承易經心學,一方面用來解釋文之心,一方面也援引之,描述作家創作之「心」。因為,作家的心是「心總要術」(〈神思〉),意謂心是一切創作的根源。作家「秉心養術」,要做到「無務苦慮」、「不必勞情」(〈神思〉)故而作家創作的心要時時刻刻保持清閒虛受的心境,才能「入興貴閑」(〈物色〉),在〈養氣〉一篇,彥和更強調「清和其心」的重要,它與「調暢其氣」的功夫同樣重要。 當然,作家的養心功夫,終究要上達天地之心。易經〈復〉卦彖曰:「動而以順行,是以出入無疾,朋來無咎。……復,其見天地之心乎?」,清楚地講明天地的心,是周而復始,一切動靜皆順行,無咎無疾,天地何心?歐陽修云:「天地以生物為心。」所以生生之謂易,天地之大德曰生。在這一層次的天地之心,是源源不絕,創造活動的本然現象。人文之有心,完全與此現象相同。馬其昶曰:「人之心,天地之心,一而已矣。」[7]最得其解。 《易經》的心學,可視作一種統整體系,接近「形而上學」的層次。由此轉化到人世間來,即人文世界講的心學。心的修養功夫問題,遂成為先秦學術的熱門課題。錢賓四在《靈魂與心》一書中,括舉《左傳·昭公二十五年》子產談心之語,子產論魂魄之定義語,子產謂:「人生始化曰魄,既生魄,陽曰魂。」云云,賓四認為先秦心學文獻始於《左傳》。[8]此處的心,又牽連出魂魄,把心學的領域擴充了。這與荀子談心,謂:「心統性情。」的說法一般,都在強調「心」的統整功夫。而《管子‧內業》云:「靈氣在心。」次云:「心靜氣理。」,又云:「凡心之形,自充有盈,自生自成。」等等的論述心之狀態與功用,在在說明了先秦心學的豐富內涵。[9] 及至《中庸》,發揮易經心學,加以具體化,用「誠」字轉化心學到德性修養,統合心學內外含意,於是,心與誠合一,便成為心學最高指導原則,遂與天地之心聯繫貫通。《中庸·二十二章》云: 唯天下至誠,為能盡其性,能盡其性,則能盡人之性。能盡人之性,則能盡物之性,能盡物之性,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,則可以與天地參矣! 在這段講誠的功夫原文裏,誠發揮極至,是可以如天地大德一般生生不息,化育萬物,也可以參透天地之心。只有心之誠,才能通達天地。所以《中庸》肯定「至誠如神」(二十四章)的境界。這個心誠的功夫,既可「見天地之心」(《周易·復·彖》),也能「上下與天地同流」(《孟子·盡心上》)當然,最終也能夠參天地之化育了。由此可知,不論《易經》的心學,或是先秦其它子學家講的心學,《中庸》總括一個誠字功夫,把心學具體化、功夫化。誠字總結心學的內外、形上形下諸般含意。 劉彥和《文心雕龍》拈出「文心」一詞,從「心」的角度以探討文學文化領域,把文心比之人心,比之天心地心,屢言「貴虛靜」、「鬱此精爽」、「文果載心」、「心生而立」、「千載心在」、「道心惟微」、「心奢而辭壯」、「心與理合」、「辭共心密」、「心以理應」、「心定而後結音」、「心術既形」等等,凡此詞彙之心概念,全部或部份引伸、轉化,無不出自《易經》為首的先秦心學。從而可知《文心雕龍》全書立論架構,來自《易經》,與易理相通。 [1] 先是,楊照明《文心雕龍校注拾遺》據黃叔琳校,馮舒校,並何焯語,校改五性。但未明注何為五性。其後,楊先生有補正之作,仍從前校,並增注,引《漢書·翼奉傳》云:「五性不相害,六情更興廢。」語為證。(見《文心雕龍校注拾遺補正》,頁300。)至此,可知作五性為是。且亦知五性六情成詞,乃漢人常言。案:今存元至正刊本、紀批本皆作五情發。 [2] 引自《漢書·翼奉傳》晉灼注,用王先謙《漢書補注》本。 [3] 諸家注五性,惟陸侃如、牟世金之《譯注》最得解,注云:五性指從肝、心、脾、肺、腎產生出來的五種性情。(參《文心雕龍譯注》,頁403。)此注已知五臟配五行,五性即五行之性。但未進一步詳解甲己合土云云之天干化合與五性相配之道理。又案《白虎通》〈性情〉總論謂有五性六情。(陳立《白虎通疏證·卷八》,廣文本頁453。) [4] 王、徐二家之辯論,詳見徐復觀〈王夢鷗先生『劉勰論文的觀點測試』一文的商討〉乙文,載徐復觀《中國文學論集續編》,頁165-184,台北:學生書局,1984年。 [5] 案自然之道一詞,易生誤解者,即「自然」。今查《周易》經傳並無自然詞彙。自然為道家主要概念,《老子》云:「悠兮其貴言,功成事遂,百姓皆謂我自然。」《莊子》一書〈至樂〉、〈德充符〉兩篇亦言自然,意謂:「自己如此。」之自然。易經無此自然詞彙。 [6] 以上劉、姚二家解,轉引自馬振彪《周易學說》,頁410,廣州:花城出版社,二○○二。 [7] 歐、馬二家注,同前引書,頁二四五── 二四六。 [8] 參閱錢穆《靈魂與心》,頁六○,台北:聯經出版事業公司,一九九四年,初版第八刷。 [9] 案《管子》一書騃雜。羅根澤《管子探源》云其中四十五篇,戰國年間人作品。〈內業〉即其中。《韓非子·五蠹》已稱舉〈兵法〉篇,今本《管子》即有此篇。屈萬里《先秦文史資料考辨》謂管子這部書一部份在先秦已經流傳了。但是否包括〈內業〉,未定。王籧常《諸子學派要詮》謂〈內業〉蓋古有其書,而管子述之。最是。 |
|||||
| 文章录入:okuc 责任编辑:okuc | |||||
| 【发表评论】【加入收藏】【告诉好友】【打印此文】【关闭窗口】 | |||||
| 最新热点 | 最新推荐 | 相关文章 | ||
| 没有相关文章 |
 网友评论:(只显示最新10条。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,与本站立场无关!) 网友评论:(只显示最新10条。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,与本站立场无关!) |
| | 设为首页 | 加入收藏 | 联系站长 | 友情链接 | 版权申明 | 管理登录 | | |
 |
粤ICP备05083455号 Copyright 2004-2005 CulChina.Net 主办:深圳大学文学院·传媒与文化研究中心 站长:孙海峰博士 |